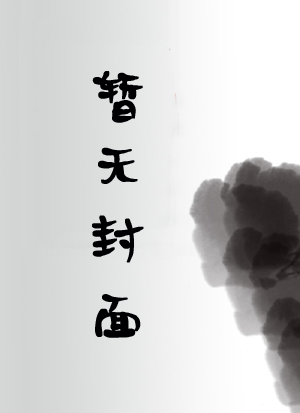番外-今生篇·【曲重起,兩不負】
成須山頂,裕天觀外煙霞萬丈。
觀內熱鬧的像是過年,嬰兒的哭啼聲響徹山間。
滿頭大汗的離恕手忙腳亂,「你們抱怎麼不哭,難道我長得這麼嚇人嗎?」
「孩子不是這樣抱的!」流風從他手裡接過來,舉著撥浪鼓慢悠悠地唱歌謠,「天有雲,地有草,平兒聽了哈哈笑……」
平兒果然不哭了。
祝清被眾人圍在中間,眉目帶著溫柔的笑意,「我來吧。」
一旁的吉瑛道,「清姑娘,你去歇著吧,我們都排著隊想跟平兒玩呢。」
祝清笑了笑,沒再堅持,隨口問道,「有看到箏兒嗎?」
離恕擡頭,「她去經房了。」
經房中,祝箏剛進門,就被容衍抱起來放在了木箱上,拉著她的手環在頸間。
「三天隻跟我說了四句話。」容衍語帶控訴。
祝箏眨了眨眼,「有嗎?」
剛剛來的路上就不止四句了吧。
她正掰著手指頭準備數一數,忽然瞧見容衍低頭湊近,趕忙捂住了他作亂的嘴。
「待會兒被人看見……」
容衍索吻不成,把她的手握住吻了吻掌心,「全觀都知道我們什麼關係了,還怕誰看見?」
就是因為知道,這裡裡外外全是熟人,讓她現在胡作非為非常有負擔。
雖然,嚴格來說,她和容衍這會兒才算得上是真真正正的新婚燕爾。
但祝箏不是故意拿喬,實在是分身乏術。
自打回成須山以後,把祝箏忙的像小陀螺一樣。
月前到盛京時,祝箏見了許多擔心她的熟人,還不等進宮向姐姐報平安,公儀灝先主動找上了門。
他一反常態的熱絡,讓祝箏帶姐姐出去散散心,順便也把平兒帶上。
條件是,容衍繼續當小太子的太傅。
容衍沒直接答應,隻道自己不會再留在盛京。
公儀灝卻好商量的很,若是容衍願意,平兒不必養在皇宮。
容衍最後同意了。
於是,容衍帶著祝箏,祝箏帶著姐姐,姐姐帶著平兒,一同回了成須山。
到了成須山,祝箏怕姐姐不適應,寸步不離的跟著,把裕天觀的每個人每條路每個樹疙瘩都介紹的清清楚楚。
平兒都快能說話了,還沒跟她這個小姨見過面,自然得好好彌補彌補,和容衍一起攬過了看孩子的重任。
但姐姐對容衍從前有幾分成見,兩人一見面便有些不對付,她在兩頭是把好話一籮筐一籮筐的說。
才終於讓姐姐把容衍看順了眼。
此外,師父知道了他們倆的事,聽聞容衍連個成親儀式都沒擺齊全,勃然小怒了一番。
整個裕天觀都張羅起了兩人的婚宴,滿山張彩掛紅,喜帖都發到了山下的鎮子上。
拜堂成親那日,師父在,姐姐在,崇明師伯的牌位也在。
等這個儀式過完,他們回到成須山已經一月有餘了。
祝箏自知最近是沒分給容衍多少心力,有些略微心虛,討好地親了親他的臉。
沒想到容衍還是不滿意,「敷衍。」
祝箏擰眉,「那怎麼才算不敷衍?」
問完便有些後悔,這簡直是白送給他一個演示「不敷衍」的機會,正想著,果然見容衍眸色轉深,腰間的手摟緊,正準備吻下來時,門上被敲了一聲。
「箏兒,你在裡面嗎?」
「阿姐!」祝箏一凜,「我、我在,我想找一本經書來著……」
她想跳下木箱,被容衍按在了懷裡。
祝清聽見房內的響動,「你一個人?」
「嗯……」祝箏剛應聲,耳尖上被吮了一口,「唔……」
祝清站在門外,這會兒還能不明白她是幾個人。
無奈道,「待會兒到東廂房找我。」
「好……」祝箏答道,「知道了阿姐,我待會兒就去。」
容衍再想溫存,瞧著祝箏橫眉倒豎地埋怨他胡來,也隻能作罷。
眼睜睜看著祝箏溜走,容衍眸中含了幾分幽怨,他這個夫君排的實在靠後,明媒正娶了還是見不得人。
次日一早,容衍把祝箏叫醒,「跟我去山下辦件事。」
祝箏高高興興地跟到山下,結果就發現要辦的事就是她。
且一連辦了好多天。
容衍被曠了好些日子,一進山莊便捉住祝箏上了賊船,天雷地火漫天縱起,恨不得把她從裡到外燒個乾乾淨淨。
雖然他長著一張欲求無甚的臉,行起這種事卻像是不知疲倦似的荒蠻。
祝箏存了補償他洞房花燭夜的心思,倒也樂得配合,隻是不分白天黑夜的實在吃不消,忍不住說了一句總不能一直在榻上待著。
後來,確實離開了榻,可……
算了……此等之事不便細說……
容衍也學壞了不少,總是愛在關鍵時候哄著她叫「夫君」。
祝箏被他折騰地哀哀嗚嗚,「大人……」「承壹……」「夫君……」來回碎碎地喊,直把容衍喊的氣息沉沉,好幾次忖不住力道,把她弄出眼淚來。
在這要命的關頭,他還能停下來擦她的眼淚,祝箏不上不下,氣的胡亂咬他一通,咬得容衍眼尾泛紅,也顧不上眼淚了,攜著她一同徹底沉入無邊溫海之中。
胡鬧一夜,天色將亮時,祝箏才沉沉睡去。
她忽然夢見了容衍。
在一個狂風怒雪的月夜。
他神色憔悴,長發散亂,穿著一件很舊的衣袍,站在高台上吹簫。
容衍已經很久不這樣打扮了,近來春風穿山,他也是萬物復甦的樣子,穿的很是惹眼悅目,在眾位師弟中一眼便能看見,有幾分扮嫩的嫌疑。
瞧著這樣陌生的容衍,她覺出一種恐慌,人說不夢枕邊人,祝箏卻在心裡覺得,她已經很久沒和這個人見面了。
簫聲停,遠處歌謠陣陣,「芙蕖面,將相骨,從此不再人間顧……」
天邊的圓月亮如白晝,眼前的容衍帶著病容。
月色映得他形銷骨立,輪廓模糊,隻看到一雙潮濕的眼睛空洞無光,唇上蒼白乾裂,毫無皿色。
風吹起衣袍,鬢間已見微霜。
兩人相向而立,容衍垂著眼眸,神采似乎暗藏些低沉,又似乎沒有。
他動了動唇,沒有發出任何聲音。
他叫她,「祝箏。」
無聲的一聲呼喚讓祝箏眼眶一酸,心緒沉重的像在經歷一場突兀的告別,一滴淚毫無預兆地落下來。
容衍伸出手接住那滴淚,握在手心裡,指尖沒有觸到她的臉,隻停在半空,潮濕的目光像霧化作的細雨。
夢中應是無知無覺,但她覺得淚痕處涼的徹骨。
「夫君……」她下意識地喚。
容衍擡眸,神色怔忡,那反應很是古怪,像是第一次聽見她這樣叫他。
天地間忽而雪停。
良久,他唇邊帶了極淡的笑意,目光卻失了焦距,像是穿透了什麼。
高天之上的月亮驟然墜落,四周籠著的光開始消散。
從前的次次相見忽現眼前,宛如宮燈在狂風中旋轉,畫面更疊替換,生動的相貌朦朧,飛揚的笑語飄散,隨風起,隨風去,漸化為一片悵然的寂靜。
祝箏莫名心慌,伸手想抓住他,卻隻觸到一片雲霧的濕冷,像徹夜未乾的淚。
「你要去哪兒……」祝箏喊了一聲。
他沒有應她。
雪月皎皎映照天地,白茫茫的一片,那抹絳紫色的身影獨入風雪中,步履從容。
狂風呼嘯不息中,修修玉身,凜凜珀光,似梅上雪融,直至消弭的無影無蹤……
有熟悉的聲音貼著耳畔響起,一聲聲叫她的名字,祝箏從夢中驚醒,急促的喘息。
容衍將她摟在懷裡,神色滿是擔憂,「怎麼了?」
祝箏翻身牢牢抱住他,把臉埋進他的頸窩,驚魂未定道,「做噩夢了。」
「夢見了什麼?」
「夢見你了……」
容衍借著月光看清她臉上的淚痕,輕拍她的背安撫著,「夢見我?也是噩夢麼?」
祝箏「嗯」了一聲,悶聲道,「我夢見你變老了,看起來很不好……」
祝箏一直以為他老了也是個仙風道骨,自得其樂的清俊老頭,沒想到卻滿是病骨支離的頹喪,讓她的心跟著抽痛。
聽到她夢見的是自己,容衍神色微微放鬆,撫著她的面頰輕聲嘆道,「等我變老了,變醜了,難道你要反悔,拋棄我這個老人家嗎?」
他一本正經的調笑把祝箏心中的惴惴難安沖淡不少,順著話音嗔道:「說不準呢。」
容衍翻身壓下來,祝箏吸了吸鼻子,「做什麼……」
「心慌。你哄哄我。」
一個細膩入微的親吻落下來,祝箏緊抓著他的手,不知道算是誰哄誰,飄搖的心終於漸漸安定下來。
天邊霧蒙蒙的月西沉,像是潮濕的眼眸低垂。
似夢中人,似眼前人。
祝箏窩在他懷中,不再去想旁的,閉著眼睛絮絮念叨些閑事讓自己分心。
「師父說,到了開春播種的季節,記得從山下帶點蘿蔔茄子葫蘆的種子回去,還問我們家有沒有別的想種的……」
容衍默了默,重複道,「我們家?」
「這裡不是我們家麼?」祝箏睜開眼睛看他,彎了彎唇角,「你想清凈的時候,我們就回家來住,平常也可以住在山上,你去教晨課,我陪著姐姐和平兒一起上課……」
她的聲音輕輕的,似廝磨的耳語,說著未來的打算。
窗上透出曦光,天邊正迎來早春的黎明。
家,真是一個好聽的字眼。
容衍有些出神,直到祝箏戳了戳他,他將人攬緊,在她發頂蹭了蹭。
「家裡……再種一棵青柑樹吧。」
「好啊。」祝箏點頭,「這次,我們選個甜一些的……」
<全文完>